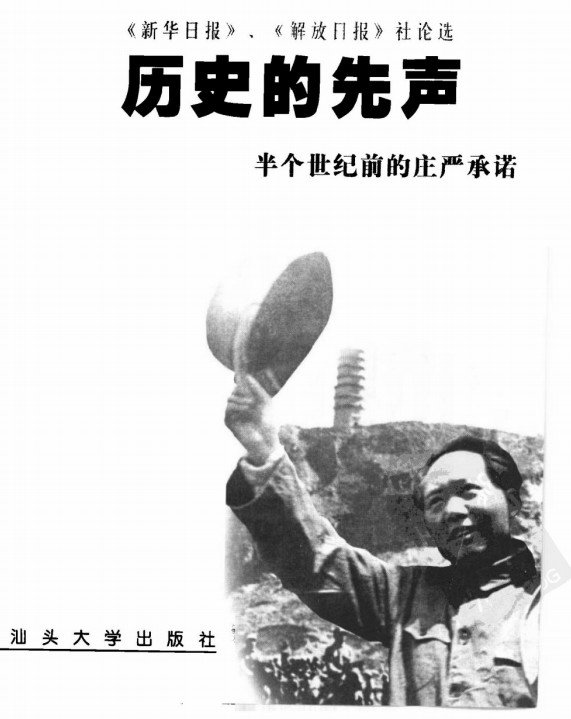 笑蜀先生編的《歷史的先聲》日前在港再版,集中再現了1940年代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刊發的毛澤東等人支持憲政民主的言論。這本書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領導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話,沒有任何“造謠誹謗”的成分,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。究其原因,應該是“討債”味道過於明顯──中共當時對民主、自由、憲政、分權、聯邦制乃至反對一黨專制的承諾,六十多年後怎麼一個都不見兌現?言下之意,現在是兌現原始承諾的時候了。
笑蜀先生編的《歷史的先聲》日前在港再版,集中再現了1940年代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刊發的毛澤東等人支持憲政民主的言論。這本書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領導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話,沒有任何“造謠誹謗”的成分,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。究其原因,應該是“討債”味道過於明顯──中共當時對民主、自由、憲政、分權、聯邦制乃至反對一黨專制的承諾,六十多年後怎麼一個都不見兌現?言下之意,現在是兌現原始承諾的時候了。
對於中共的進步承諾,近來反憲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楊曉青的文章解釋說,這是當時“對敵斗爭的策略”。換言之,這本來是一套騙取民心的謊話,是不能當真的﹔自由派別“拉大旗作虎皮”,拿這個來要挾現政權。這套言論和承諾當時確實“欺騙”了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,加深了他們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厭惡、對貌似反專制的共產黨的信任和親近。在那些因此而堅持留在大陸、拒絕蔣介石從海峽那邊拋來的橄欖枝、甚至千裡迢
迢從太平洋彼岸趕回來“報效祖國”、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磨難乃至冤死的高級知識精英看來,這套承諾很可能更像一個騙局。
但是,從不少歷史資料來看,諸如此類的“陰謀論”或“陽謀論”是沒有多少根據的。假如當時國民黨願意坐下來好好談,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憲政方案去做,並似乎已經採取了一定的實際行動。這也很好理解,因為在內戰開打之前,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﹔相比老蔣的盲目樂觀,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倒是相當清醒。更不用說從中共建黨到“西安事變”,從來只有國民黨“老大”打共產黨“小弟”的份﹔雖然中共在八年抗戰中養精蓄銳、不斷做大,但還不至於有後來三年打垮國軍的自信。國共合作對它是有利的,提倡憲政、民主、分權、聯邦的效果是限制國民黨老大的權力,對它也是有利的。國民黨要回到抗戰前的一黨專政格局、重新“統一”中國,共產黨則只要能“劃江而治”就很滿足了,何樂而不為呢?
因此,你可以說中共當年的憲政言論是一種“策略”,至少不能排除宣傳“策略”的成分,但是沒有必要把“策略”解讀成謊言。毛澤東當時主張憲政,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,但這也不是說他就是一個“憲政斗士”﹔他顯然不是,但是當時的國共實力格局使得他認為憲政對中共有利,於是就支持憲政。
今天,我們已沒有必要糾結於中共支持憲政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。這個問題已經不相關,因為現實很清楚,1949年之後,中共不僅沒有兌現當年的承諾,而且憲政、新聞自由、三權分立、聯邦制乃至公民社會都成了報刊中不能出現的“敏感詞”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?這個道理簡單──格局變了。國民黨掌權的時候,憲政是限國民黨的政﹔現在還提憲政做什麼?那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?
其實,沒有兌現的豈止是1940年代的承諾,1982年憲法不也承諾了許多權利嗎?有幾條是真正兌現的?紙上的規則和“潛規則”大相徑庭,這種現象在大陸是再正常不過了。
你可以從道德上批判它出爾反爾,但是沒有實力支撐,道德批判是蒼白無力的。當我們興高採烈地把所有生殺大權都交給一個我們認為“先進”無比的政黨,我們已經把自己降格為“政治奴隸”。主人能欠奴隸什麼“承諾”?即便以前做過承諾,那確實是出於“斗爭需要”,不得不如此﹔現在事過境遷,兌不兌現我說了算,不兌現又能怎麼樣?當年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,農民歡欣鼓舞跟著黨走﹔1950年代初,也確實分了幾畝地。但是沒幾年,土地又統統收回來,歸“公社”了,你難道還能不交?不要忘記,“國家”是干什麼的,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。
你現在站起來向主人“討說法”,那就表明你已經不是奴隸了。不過,主人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化,他還和從前一樣把你定位成奴隸。他的主流邏輯是:只要你還沒有實力和我叫板,就慢慢等著吧。不要忘記,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!這個江山是我們先輩打下來的,當初也是在你們擁戴下得到的。
每每看到今日中國的困境,便不禁聯想起往日失去的機遇。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機會!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機會!國共二次合作何嘗不是一次真正的機會!但是我們一次又一次丟失這些機會,不能只怪慈禧或醇親王,不能只怪袁世凱、孫中山、蔣介石或毛澤東。畢竟,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,是我們把他們扶上位的﹔至少,他們是在我們的普遍麻木和無動於衷下執掌權力的。我們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,是何其興高採烈、毫無保留,但是等到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正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,“被推翻的舊政權總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權更好”,一切為時已晚﹔這個民族已經把自己的全部命運交給它的新主人,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難。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選擇讓我們淪落到今天,每一次都讓我們陷入離憲政更遠、更深的漩渦……
也許,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貴學費。農民的輕信是無可指責的,但知識精英的天真爛漫是不可原諒的。長期浸淫在儒家正統的教條主義思維當中,中國知識分子對權力政治學從來沒有任何概念。我們從來只認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、好人、壞人。壞人便是絕對的壞,必欲打倒並踏上一隻腳、令其“永世不得翻身”而後快﹔好人便是絕對的好,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賦予其一切生殺大權,並天真地期待它作出過的“承諾”,而不知道這樣的“好人”即便有也鳳毛麟角,當你手裡已經沒有任何底牌的時候,你憑什麼相信他會兌現承諾?
正如托克維爾對中央集權時的法國觀察的那樣,政治專制必然造成國民的政治幼稚,因為他們得不到由政治實踐走向政治成熟的機會。因為國民幼稚輕信,這樣的國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險,因為它容易爆發革命。一遇到“壞人”政府,人民就郁悶憤激﹔一遇到“好人”的承諾,人民就投懷送抱。專制政體使之無法近距離比較“好人”、“壞人”及各種承諾,並做出理性的政治選擇。
不夸張地說,近代中國所有“更壞”的政府都是因為國民(尤其是社會精英)的不智選擇而登場的。每當我讀到某個滿腔熱血的歸國精英慘遭“反右”或“文革”迫害的悲劇,心裡就泛起一陣悲哀。這是一個幼稚政治傳統所得的報應,因為他們所憧憬的烏托邦,其實就是一個公權不受限制的地獄。
當代中國大陸的憲政意識已今非昔比,約束公權的必要性已經成為官民常識,但是深陷於威權政治的不幸遺產之中,憲政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。《歷史的先聲》把中共曾經做出的憲政承諾再度呈現在我們面前,與其說是提醒執政黨兌現早已過期的承諾,不如說是提醒每一位讀者:承諾是靠不住的。更准確地說,它對每一個生活在大陸的人提出了關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問題:如何兌現執政黨對你做出過的承諾?要讓當年的承諾成為今日的現實,你該做什麼?